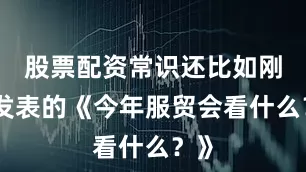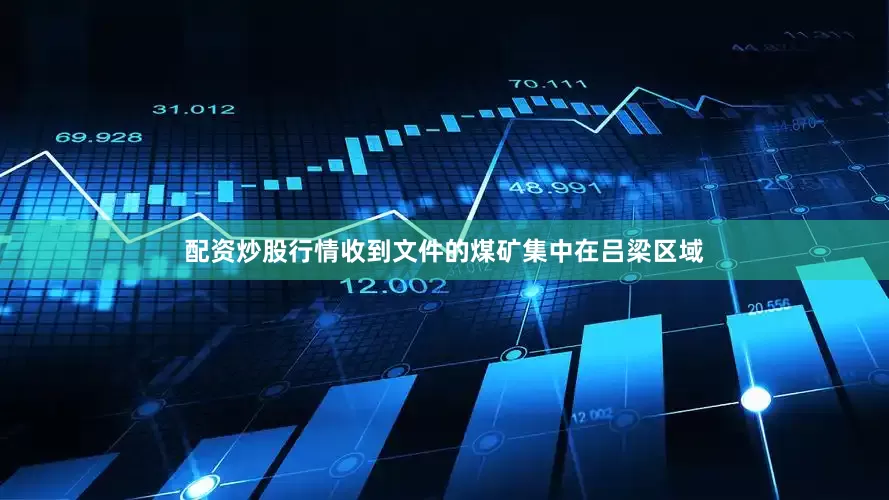说个好玩的事儿。
你要是在大街上瞅见俩人,干着一模一样的活,一个月底能盘算着下馆子,另一个却在琢磨着怎么跟房东开口,能不能宽限几天。
这场景,放哪个公司都得炸锅,得叫“同工不同酬”,得闹上热搜。
可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一线执勤的队伍里呢?
嘿,那就成了“用人模式创新”。
昨儿个刷视频,又看见辅警小哥徒手夺刀的场面,底下评论区清一色的“英雄”“帅爆了”。
可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却是:这哥们儿,是哪种“辅警”?
他的合同,是跟谁签的?
这念头挺扫兴的,我知道,但它比视频里的热血更接近现实的骨感。
咱们聊的这个辅-警-待-遇,简直就是个俄罗斯套娃,一层套一层,每层都有新“惊喜”。
先说那个最没影儿的群体,“临时工”。
这仨字儿一出来,味儿就对了。
他们是公安系统的“幽灵兵”,专门出现在大型活动、节假日安保现场。
你把他们当成是共享单车就成,扫码(签个临时协议)就骑,用完(活动结束)就锁上,往路边一扔,下次谁用谁再扫。
工资按天给,今天干完,明天有没有活儿,全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。
我认识一小伙子,前年音乐节干了三天安保,暴晒,喊哑了嗓子,到手几百块。
他跟我说,最难受的不是累,是那种感觉自己像个工具,用完就被扔在一边,连声响儿都没有。
这哪是螺丝钉啊,这就是块补丁,哪里破了贴哪里,贴完了随时能撕下来。
往上一层,是队伍里的大多数,也是最拧巴的一群——“劳务派遣”。

这帮兄弟可太难了。
他们穿着和正式警察差不多的制服,干着巡逻、蹲守、甚至抓捕的活儿,可他们的人事关系,却挂在八竿子打不着的劳务公司。
你懂这意思吗?
就是你给张三家看门,结果工资是李四家发的,张三家吃肉,李四给你口汤喝,还告诉你得知足。
我一哥们儿,小陈,就是劳务派遣。
刚入行那会儿,一米八的大个子,眼里全是光,觉得这身皮就是正义的化身。
干了两年,那光让他自己给掐了。
有次喝酒,他红着眼圈跟我说:“哥,你知道啥叫‘编外人员’吗?就是出事儿了,你是‘编制外’的人员;有荣誉了,你是编制‘外的人员’。好事儿永远隔着一层玻璃,你看得见,就是摸不着。”
他们就像是西游记里没背景的妖怪,被一棒子打死;而那些有背景的,犯了天大的事儿,最后也就是被领回去“严加管教”。
这种不公平,比工资条上那几百块的差距,更诛心。
最后,才是站在金字塔尖的“直签辅警”。
这批人,是公安局的“亲儿子”,是过了独木桥的幸运儿。
他们是正儿八经跟单位签合同的,工资福利向民警老大哥看齐,五险一金交得你心里踏实。
更重要的是,他们脑袋上悬着一根胡萝卜,叫“转正机会”。
虽然这机会也渺茫得跟中彩票似的,但有,总比没有强。
他们是整个辅警队伍里的“天龙人”,是小陈他们做梦都想成为的样子。
所以你看,同样是“辅警”,这内部早已分化成了三个不同的物种,呼吸着不同的空气。
这事儿赖谁呢?
赖预算,赖编制。
正式编制这玩意儿,跟北京户口似的,金贵得很。

可活儿越来越多,怎么办?
“劳务派遣”这个天才发明就诞生了。
它完美地解决了“既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”的千古难题。
用最低的成本,换取最大的劳动力,至于这批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和尊严,那都是可以被优化的“管理成本”。
有人可能会说,深圳不是改革了吗?
搞了辅警分级,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儿。
是,深圳有钱,当然可以玩“高配”。
可你让一个西北小县城去学深圳?
那不等于让一个吃糠咽咽菜的去学人怎么吃法式大餐嘛,学不会,也没那个本钱。
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,是心态的事儿。
我们习惯性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,在辅警这个群体里,更是把这种逻辑发挥到了极致。
我们一边要求他们无私奉献,一边又在制度上告诉他们“你们不一样,你们是临时的”。
这种精神分裂,迟早要出问题。
所以,以后在街上再碰到他们,别光看那身衣服。
衣服底下,可能是一个月光族,一个迷茫的年轻人,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
他可能刚处理完一地鸡毛的纠纷,也可能马上就要冲向未知的危险。
我们这个社会,给予他们的关注和保障,实在是太少了。
而一个连自身保障都朝不保夕的人,你又怎能苛求他,时刻都能给你最坚实的安全感呢?

这事儿,想想都觉得挺分裂的。
上海的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证券配资平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正加快推进主体结构施工
- 下一篇:没有了